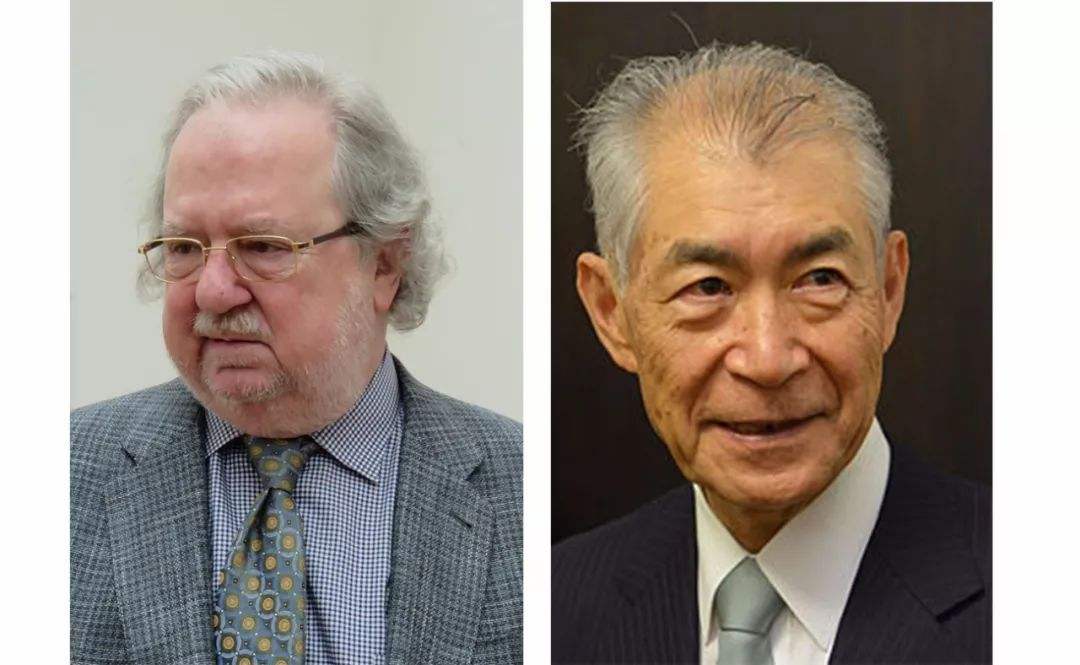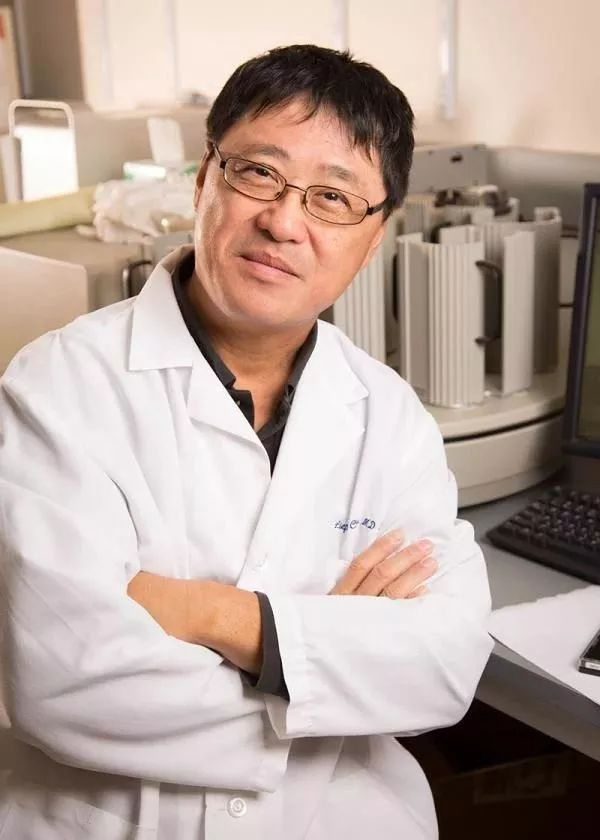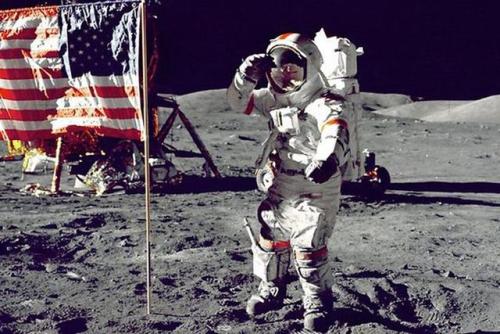諾獎評選未來會面臨更多爭議
癌癥免疫治療能夠取得重大進展,離不開無數(shù)科學(xué)家的艱辛探索。此次獲獎的美國科學(xué)家詹姆斯·艾利森和日本科學(xué)家本庶佑成就斐然,獲獎并無多大爭議,在中國的爭議主要是華人科學(xué)家陳列平是否應(yīng)獲得諾獎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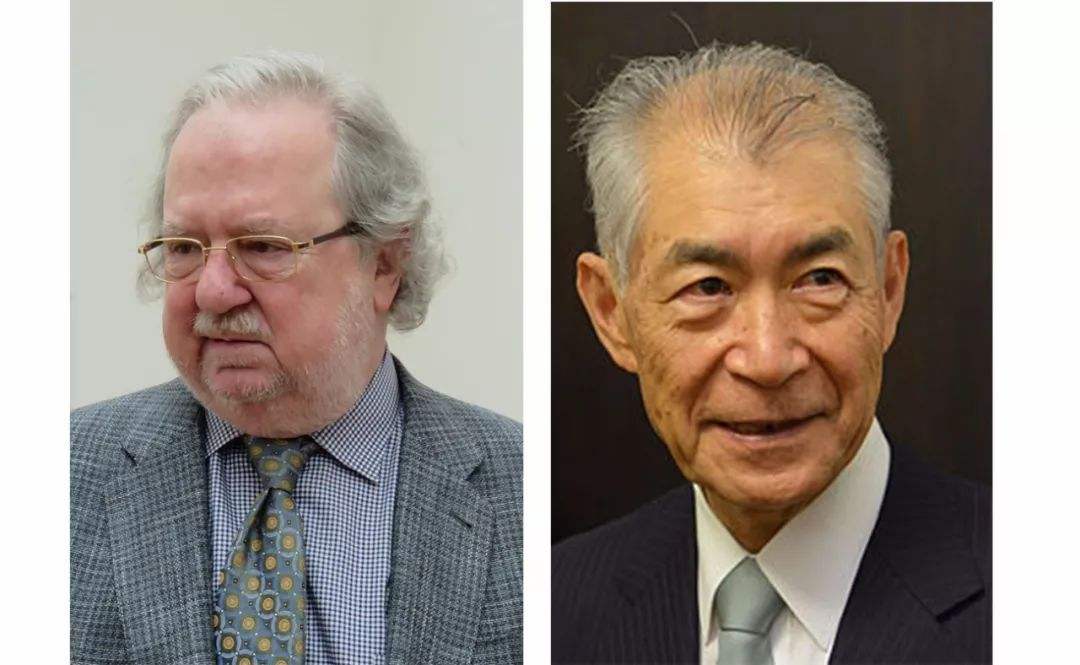 詹姆斯·艾利森和本庶佑
詹姆斯·艾利森和本庶佑陳列平教授在腫瘤免疫領(lǐng)域的貢獻的確得到了國際認(rèn)可。2017年,陳列平、詹姆斯·艾利森、本庶佑、戈登·弗里曼和阿琳·夏普5位科學(xué)家,因在腫瘤免疫領(lǐng)域做出的開創(chuàng)性工作共獲沃倫·阿爾珀特獎,陳列平成為繼簡悅威、屠呦呦之后,第三位獲此獎的華人學(xué)者。
此次未獲諾獎,不僅國內(nèi)的同行為他鳴不平,他也不滿意——“首先CTLA-4并不是詹姆斯-艾利森發(fā)現(xiàn)的……艾利森只是首次將其作用聯(lián)到癌癥治療方面,而本庶佑雖然發(fā)現(xiàn)了PD-1,但是機制并不是他發(fā)現(xiàn)的,腫瘤治療更是與他無關(guān)。但這兩位在宣傳鼓動方面確實勝出我很多……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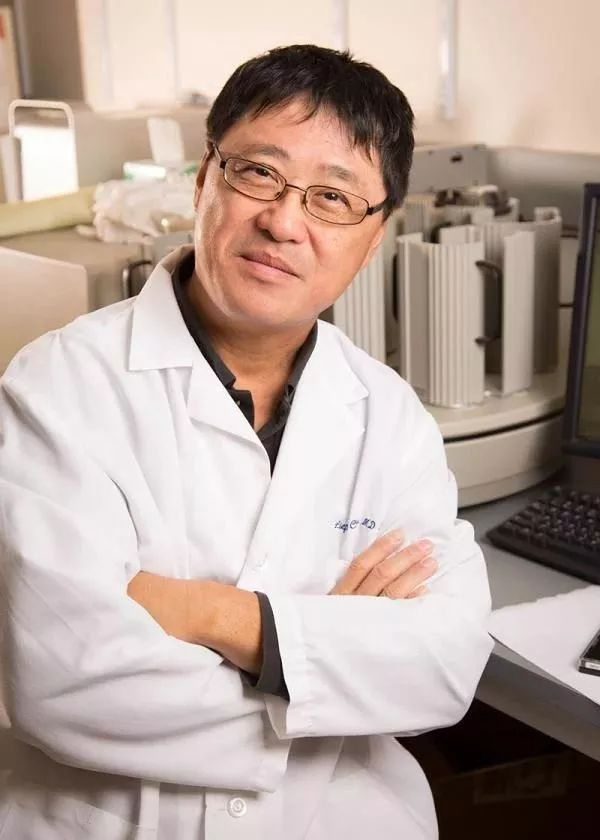 陳列平
陳列平
諾貝爾文學(xué)獎有爭議不稀奇,為何諾貝爾科學(xué)獎也會有爭議呢?這不僅是因為世上沒有完美的評選標(biāo)準(zhǔn),更因為諾貝獎評選的一些規(guī)則“過時了”。
在科學(xué)發(fā)展早期,科學(xué)家憑借個人的力量就可以取得突破性成就,牛頓、達爾文、居里夫人、愛因斯坦等人即是如此,但是到了現(xiàn)代社會,科研離不開團隊合作——大到需要成千上萬科學(xué)家合作的科學(xué)工程(如阿波羅計劃),小到某個具體的科學(xué)領(lǐng)域(如細胞免疫治療),幾乎每一項成就都是眾多科學(xué)家前仆后繼,集體協(xié)作的結(jié)果。到底哪幾個人的貢獻更大,越來越難分辨。
而諾貝爾科學(xué)獎每項獲獎?wù)卟粫^3個人,這就需要委員會絞盡腦汁從一個領(lǐng)域的杰出科學(xué)家中選定一位、兩位,頂多三位獲獎?wù)摺R欢ㄒ页鼍唧w的個人頒獎,諾獎的這種結(jié)構(gòu)性缺陷很容易引發(fā)爭議。
在加州大學(xué)天文物理學(xué)家布萊恩·基亭看來,如此評獎不僅不公,也強化了外界的刻板印象——認(rèn)為科學(xué)是由一兩位孤獨的天才進行,忽視了背后支持他們的科學(xué)網(wǎng)絡(luò)。
可以預(yù)見的是,隨著科研機構(gòu)合作的加深,跨領(lǐng)域科研的發(fā)展,未來諾獎科學(xué)獎的評選,還會有更多“評獎是否公正”,“憑什么他不能得獎”的爭議。
在為陳列平抱不平之后,更該想想他當(dāng)初回國為何不受待見
諾獎評選雖有爭議,爭議主要在于一些人覺得有的科學(xué)家也該得獎,不得獎是諾獎的損失。不過,諾貝爾科學(xué)獎的中立、公正和權(quán)威依然深入人心,一國諾獎得主的數(shù)量也是衡量一國科技實力的重要指標(biāo)。
為本國科學(xué)家抱不平容易,國人可以抱怨“少了陳列平一個諾獎”,其他國家的人也可以抱怨少了本國某某科學(xué)家一個諾獎。在抱怨之后,更該反思的是,為何陳列平的主要研究成果不是在國內(nèi)取得的。
在2017年獲得沃倫·阿爾珀特獎后,陳列平曾接受過《知識分子》的采訪。他表示,由于腫瘤疫苗在臨床治療的失敗,該領(lǐng)域在2000年初處于低潮中。2006年,經(jīng)過多年籌備,他的抗PD-1/PD-L1抗體藥物才在美國開始了I期臨床試驗。
 接受化療的患兒
接受化療的患兒兩年之后,I期臨床結(jié)果喜人。陳列平本打算在國內(nèi)嘗試開展類似的研究,但國內(nèi)學(xué)術(shù)界對此項研究反應(yīng)冷淡,從他實驗室回國的博士后也在經(jīng)費申請上遇到很大挑戰(zhàn)。
到了2012年,抗 PD-1藥物 I/II 期臨床試驗結(jié)束,結(jié)果顯示抗 PD-1藥物對腫瘤治療效果非常明顯。
他打算回國組建創(chuàng)新團隊,進行大型科學(xué)項目轉(zhuǎn)化研究,但十多個評委(一半以上都是院士),沒有認(rèn)可他工作的重要性,結(jié)果是申請的經(jīng)費被砍掉了90%。
2013年,陳列平終于從母校福建醫(yī)科大學(xué)和當(dāng)?shù)卣@得了支持,這才建起了自己的實驗室。
陳列平坦言,“在耶魯大學(xué),我可以建自己心中理想的實驗室,做想要做的研究,沒有很多行政干預(yù)。這一點在國內(nèi)卻有些不同,如果國內(nèi)科學(xué)家這樣做,需要面臨更大的壓力,因為中國科研政策的導(dǎo)向性很強,今年做什么,明年做什么,都已經(jīng)設(shè)計好,否則很難拿到經(jīng)費。在你被孤立的時候,是否仍能做出新的東西,這需要經(jīng)受極大的考驗。”
可以想象,如果陳列平一直在國內(nèi)搞研究,只鉆研自己感興趣,領(lǐng)導(dǎo)卻不關(guān)注的領(lǐng)域,研究經(jīng)費可能都沒著落,更不要說取得今日的成就了。
沒有合理的科研評價機制,投入再多也沒用
近年來,我國對科研發(fā)展非常重視,研發(fā)投入不斷增加。2017年,我國研發(fā)經(jīng)費投入總量為17500億元,比上年增長11.6%。從全球看,中國研發(fā)經(jīng)費投入總量僅次于美國,居世界第二位。
中國雖然也有諾貝爾科學(xué)獎的獲得者,但中國在研發(fā)上的投入和諾貝爾獎的產(chǎn)出完全不成比例。日本18年18個諾貝獎得主的成就,也讓一些人感嘆“何時我們才能像日本一樣多次獲獎”。
有樂觀者認(rèn)為,一些國家諾貝爾獎得主多,是因為他們之前科研投入的多,科研基礎(chǔ)好。人家的科學(xué)家在十米跳臺上搞創(chuàng)新,我們自然比不過,但只要保持定力,持續(xù)投入,過些年我們高校中的科研機構(gòu),也會跟下餃子一樣產(chǎn)生諾貝爾獎得主。
錢花到位了,就能培養(yǎng)出諾貝爾獎得主嗎?恐怕不一定。要知道,一個真正意義上的重大發(fā)現(xiàn)或者原創(chuàng)成果,需要的是以10年甚至更長時間為單位的反復(fù)探索、糾錯,然后才可能完善。
目前的科研評價體系,由政府主導(dǎo),“沒有等待的耐心”,其實把科研當(dāng)成政績一樣考核,本身就缺乏科學(xué)性。
正如陳列平所說,國內(nèi)科研缺乏原創(chuàng)環(huán)境,很多中國科研人員都是在追蹤熱點研究。中國相關(guān)政策亦在鼓勵跟進,這可能是方向性錯誤。
如果說諾獎評選引發(fā)爭議是遇到了科研發(fā)展中的新問題,那我國的科研評價還有不少基礎(chǔ)性問題待解——科研的行政導(dǎo)向有必要,但朝向哪里,怎么做,科學(xué)家也要有發(fā)言權(quán)。畢竟,一旦方向錯了,投入再多,也不會有多少原創(chuàng)性產(chǎn)出,更不要說諾獎級的創(chuàng)新。